民族性和时代性是我们构建当代中国道德信念体系的两个基本原则。如何实践这两个原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很多时候人们可能会满足于将中国传统的理念和现代西方流行的理念简单地拼接、堆砌在一起,以为这就是兼具民族性和现代性的精神文化产品了。但如果我们希望构建的是一种自洽的,自成体系的道德信念的话,就必须从逻辑推演的阶段就将体现民族性和时代性的各种因素统一起来。
一方面,我们需要将祖先几千年传下的充满智慧和温情的道德文化中有潜质的部分撷英萃菁,推衍阐释,重新解读,使之合乎现代文明的潮流,适应当前社会的需要。另一方面,我们需要为现代人类文明所公认和珍视的各种理念找到符合中国文化特征和中国人思维方式的逻辑依据。近代以来诸多国学大师、政治精英在前一个方面的著述早已珠玉缤纷,后一个方面却常常被我们所忽视。

譬如自由、平等、民主、法治这些理念,尽管自百多年前西学东渐时便已由西方传入中国,早已为智识学界所接受,报刊媒体上寻常得见,普通国人亦耳熟能详,然而时至今日却远远谈不上在中华文化的土壤中生根发芽。无论人们的日常生活,还是企业的经营活动、政府的决策执政,常常都很难想到要从这些理念出发。究其原因在于这些理念纯属移植而来,我们得其果而未得其本。
所谓自由、平等、民主、法治虽说是近代民主政治的产物,但它的理念却根源于西方基督教的信仰体系和世俗秩序意识。
基督教神学从亚当、夏娃的“原罪”推导出“人性恶”,为法治主义、权力制衡和有限政府提供了逻辑起点。基督教徒认为上帝所立的神圣法和自然法高于统治者所立的实证法,世俗的秩序必须服从上天的秩序,这为依法治国提供了思想渊源。
上帝与亚当订立了人类第一个契约:只要他遵守上帝的诫命就可以得到永生。但是亚当夏娃违背了这个契约。上帝惩罚了他们之后,又与救世主耶稣订立了一个契约:只要他替人类献出自己的生命,那么人类就会得到上帝的宽恕并获得永生。据《旧约全书》记载,上帝还曾与犹太人的先祖或领袖人物立约。这就是权利、义务、信用等现代理念的重要基础——契约论。
尽管亚当与夏娃犯了罪,但他们毕竟是上帝按照自己的模样造出来的,这就意味着,每一个人都是由上帝而来,都是平等的。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的“犯罪”又意味着:人是自由的。因为从法理来说,没有主观意志的选择自由就不构成有罪。
理性时代到来,基督教退出统治地位之后,它的那些理念却保留了下来,并且成为现代人类文明的精髓。
当我们艳羡西方社会文明,将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照搬回来的时候,这些文明果实的根却仍留在它的故乡,未能,也不可能移植回来。因为我们自有根植于中华大地数千年的传统文化,不论是从社会工程的艰巨性还是从民族文化的自尊心来讲,都不能以基督教文化随便取代。这就是清末至今一百多年来,尽管先知先觉的精英人士呕心沥血,不断呼吁和传播民主法治思想,却成效不显的原因。
那么是不是中国人就不能谈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些现代人类文明的成果是全人类都有资格享有的,也必然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思想质素。只是如果我们希望这些理念在我们国家生根发芽,就必须从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寻找资源,寻找到能够为中国人所接受的逻辑,构建其可资立足的合理性、合法性。这并不是说,我们要牵强附会地从传统文化和儒家原典中强行找出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来,而是说要以传统伦理道德中的某些道德信念为起点,比如“仁”、“义”、“礼”、“信”、“忠”,加以扩展和推衍,得出肖似的概念。
经过中国传统价值观通变阐释而来的当代中国道德信念,以及由这些道德信念生发出来的其他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人群的行为规范,必定具备了有别于西方价值观的内涵。由于我们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均来自于不同于基督教文化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有着完全不同的逻辑推证过程,这就从根本上打破了西方所谓“普适价值”的话语权垄断。所谓“中国特色”即在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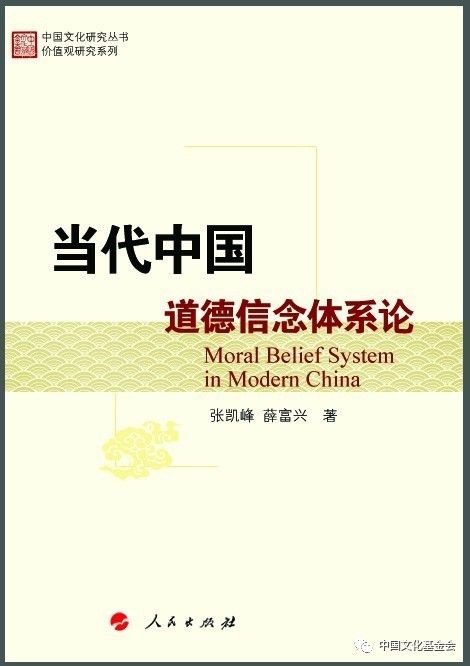
作者,张凯峰、薛富兴,该书由中国文化基金会组织课题研究,人民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