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来,历史就被划分为两大类:民族史和世界史。世界史最初指外国的历史,但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史更多指跨文化交流的历史、全球史。本文认为,世界史应该既包括前者,也涵盖后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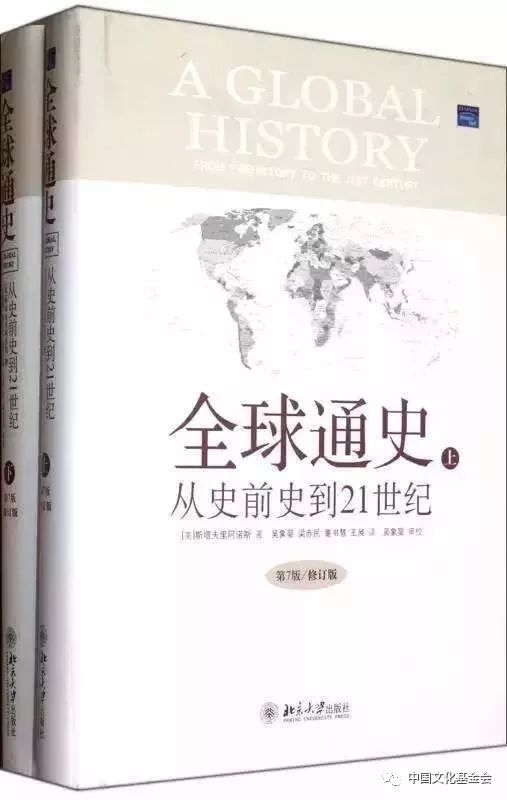
▍英国和中国的新趋势
在晚近世界史或全球史的写作和研究过程中,美国人最为积极,从威廉·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到杰里·本特利的《新全球史》,一直引领时代潮流。相对来说,英国和中国的反应是比较慢的。于尔根·奥斯特哈默在《牛津历史写作史》“世界史”条目中写道,世界史和全球史的兴起是20世纪80年代的新现象,90年代才开始引人注目地发展起来。世界史的兴起、发展和专业化最初主要在美国,直到作者撰写该条目,即2010年时才有少数国家开始赶上。麦克·本特利在回顾英国当代历史写作时说,我们正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环境的变化使我们需要“世界史”,需要关于全球环境、食物、服装等方面的历史。我们需要进入这块条件与限制并存、近乎混乱的研究领域,并充分意识到将不列颠同美国或欧洲的发展孤立开来会越来越困难。
但近年无论英国还是中国,变化都很大。伯明翰大学历史系从事中国史研究的娜奥米·斯坦登教授说,直到2000年,英国高校历史系几乎还没有专门从事中国史研究的教师,中国史只是以文学为主的传统汉学的一部分,但到2013年英国已经有20多所高校的历史系设立了中国史的教职。英国华威大学、牛津大学在2007和2011年相继成立全球史研究中心。英国学者迅速将全球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付诸实践,2013年华威大学的乔治·列洛教授推出了《棉:创造现代世界的织物》,2015年牛津大学的彼得·弗兰克潘教授出版了《丝绸之路:一部新世界史》。
中国的情况与英国有所不同。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大学教师为数不少,吴于廑先生还在80年代初提出了“整体世界史观”,即在关注人类历史由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更迭发展的同时,也要重视人类历史从分散到整体的发展。整体世界史是对传统世界史即外国史的补充,而非替代。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头十年,中国的世界史教学和研究出现了一个低谷。直到2012年世界史成为新的一级学科之后,世界史学科才迎来了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我国的全球史研究起步相对较早,早在2004年首都师范大学就成立了全球史研究中心,2014年北京外国语大学也成立了全球史研究院。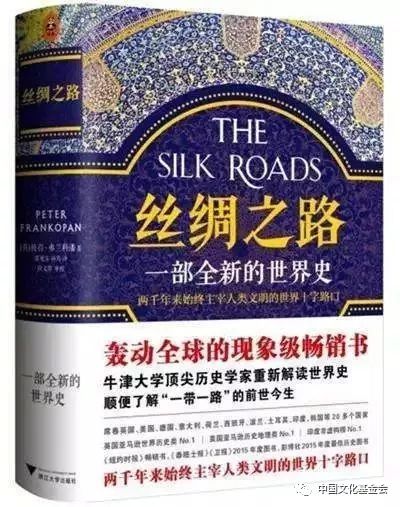
▍民族史和世界史的对立
那么,我们需要探讨,为什么英国和中国对八九十年代兴起的世界史和全球史反应比较慢,而最近又跟进较快呢?我觉得其中的原因可能有相似之处,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两个国家都存在着世界史和民族史的对立。
英国的世界史深受启蒙运动的影响。启蒙思想家认为人类有共同的理性,人类历史发展有着共同的规律,通过历史研究人们可以发现这些规律。休谟、吉本等人是这种传统的代表。后来从德国引进的历史主义,一方面表现为民族史学,另一方面表现为严格的史料考据。但是英国人最开始接受德国的史学思想就是一分为二的,以阿克顿勋爵为例,他认为在方法方面必须坚守德国式的史料考据,但作为一个著名的自由主义者,他又认为在历史的本质方面不能像德国人一样,将历史简单地等同于过去,历史学家应该有现实关怀。
到后来,英国的世界史和民族史交替上升,比如说20世纪上半叶的汤因比、巴勒克拉夫等人,他们延续了英国世界史的研究路径。剧烈冲突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牛津大学著名历史学教授H.R.特雷弗-罗珀对汤因比进行了系统的批判,认为尽管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很畅销,但对于专业历史学家来说,它是“不真实、不合理、教条式的”。从他开始到G.R.埃尔顿,实证学派逐渐占了上风,事实上埃尔顿比兰克还兰克。在这个时候谁提倡世界史和全球史都会遭到怀疑或批判。因为历史研究要立足于原始材料,否则就没有发言权。
中国也存在类似的冲突。中国的世界史是从苏联引入的,受苏联教条式“马克思主义”史学,特别是“五种生产方式”的影响,史学家的任务是探讨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因此要研究外国的历史。正因如此,从建国初到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对世界史是比较受重视的。奥斯特哈默甚至认为,除了美国之外,最大的世界史工作者群体可能在日本和中国。中国的民族史传统也来自德国。受德国历史主义影响的历史学家如傅斯年认为,中国历史学家应致力于中国史研究,因为中国有丰富的历史材料和史料批判的历史传统。在他们看来,在中国做世界史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资料条件是不够的。
有学者将中国近百年的史学争论归结为史观派和史料派之争,从建国初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史观派是占支配地位的,八九十年代则是史料派复兴并大有一统天下之势。王学典先生说:“进入1990年代后,史观派的学术史地位就越发无足轻重,乃至可有可无了。”事实上,世界史研究工作者大多属于史观派,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中国的世界史在世纪之交的前后10年步入低谷。
但现在这个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趋势变得越来越明显。在全球化的时代不可能不研究世界史,因为世界史是促进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之间相互理解、相互沟通的重要工具。如果说民族史的功能是培养民族认同和爱国主义的话,世界史则是一种“国际教育”,两种缺一不可。其次,西方学界对历史的认知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兰克史学占支配地位的过去,人们认为历史只是以研究过去为目的,但现在大多数学者认为历史学还具有道德教育的功能,它应当关注当下。
从《棉:创造现代世界的织物》和《丝绸之路:一部新世界史》中,可以明显感到两位作者正力图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关注被历史所遗忘的人群和地区,探讨历史与当下的关联。尽管两位作者大量依赖甚至主要依赖二手文献,但丝毫不影响其著作在学界内外获得如潮好评。当人们不再只是从方法或技术的层面去评判历史研究的高下时,心胸就会变得开阔一些,不再像过去那样狭隘极端。再次是资料条件的改善。过去由于受资料条件的限制,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常不得不借助二手资料,因而从专业研究的角度很难达到原创水平。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很多资料网上都可以找到并下载,现在的问题恐怕是下工夫读的人还不多。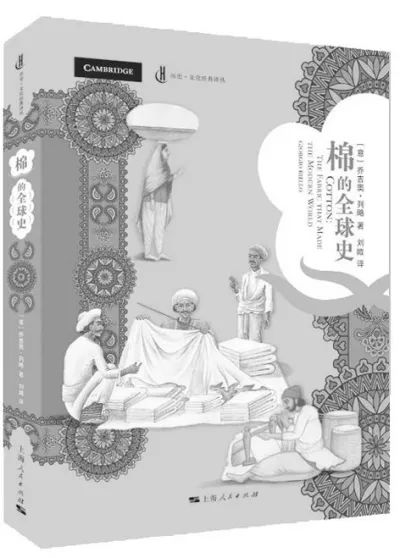
▍世界史研究破局之探讨
民族史与世界史的长期对立是我国世界史研究发展的重要障碍,那么该如何破局?这是我们目前真正需要关心的问题。现在西方学者中不少人提出世界史复兴,对此我深表疑虑。如果直到今天我们还把历史当成哲学来做的话,世界史将永远被人看不起。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不管是世界史还是民族史,都应该从原始材料做起。
如何破局?首先,要从努力提高我们自身的专业研究水平开始。我个人倾向于将世界史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意义上的世界史,即外国史,另一类是晚近出现的“新世界史”,即以跨文化交流为中心的全球史。前者应更重视具体问题研究和实证研究,虽然全球史可以更多地利用综合,但也需要有所取舍,尽可能将全球视野与具体问题研究相结合。同美国全景式的全球史相比,英国全球史研究的对象更具体,问题意识更明确,这一方面反映了英国经验主义史学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全球史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的表现。
我国世界史学界的全球史研究起步并不算晚,但到目前似乎还停留在全球史的内涵、意义和可行性争论上,这些争论既反映了一部分学者对学理问题的偏好,也反映了一部分学者对宏大叙事的不信任。我个人认为,吴于廑先生20世纪80年代的整体世界史研究值得借鉴。他不仅提出了整体世界史观,而且围绕整体世界史中的几个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具体的探讨,比如前资本主义时代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矛盾与交往,十五、十六世纪整体世界史的初步形成及其动因等。从某种意义上,笔者认为,吴于廑先生的整体世界史就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史。
其次,将个人的学术专攻放入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之中,进行历史比较研究。R.I.穆尔是著名的英国中世纪欧洲文明史专家,也是一位世界史学家,麦克·本特利主编的《史学史指南》中“世界历史”条目就是由他撰写的。他认为,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全局来看,中世纪是欧亚文明大发展、大转型、大分流的时期。从公元1000年左右开始,欧亚大陆的农业不仅空间范围扩大,而且生产和经营更为集约,从而为以城市为基本特征的文明扩张奠定了基础。
但是,经济集约化和社会复杂化也对古代社会遗留下来的价值体系提出了挑战,使得作为传统价值体系守护者的文化精英面临危机。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东西方文化精英以不同的程度、不同的方式对古代典籍进行了再诠释,从而创造出适应各自环境的新的价值体系。在他看来,12世纪是欧亚大陆前近代传统确立的时期,是人类文明经历的第一次“大分流”。
布鲁斯·M.S.坎贝尔是著名的中世纪英国农业史专家,不久前转向研究中世纪晚期英国生态环境的变化。他将自己新的研究成果置于同一时期欧亚大陆的大环境中思考,于2016年推出了《大转变:中世纪晚期世界的气候、疾病和社会》。在他看来,13世纪后期开始的气候变冷、大瘟疫给亚欧大陆带来了普遍的危机,尤其是人口锐减和经济萧条,迫使亚欧大陆各地区做出相应的结构调整。以英国和荷兰为代表的西北欧地区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如混合农业容易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在农产品价格下跌时发展手工业,发展波罗的海、北海和大西洋贸易等,最终成功地完成了大转型。因此,在他看来,彭慕兰所说的“大分流”根源于中世纪晚期的大转变。从这点看,民族史与世界史并非是截然对立,而是可以相互补充的。
再次,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建设世界史学术共同体。传统的史学研究是个性化的,一个人、一支笔足矣,但当今的世界史,尤其是全球史研究仅凭个人之力已远远不够,需要更多发挥学术共同体的作用。
列洛教授在《棉:创造现代世界的织物》“引言”中坦陈:“尽管有可能获取大量的信息、解释和史学文献,全球史仍难免经常出现偏见。欧洲(西方语言)的学术和档案资料是问题的核心。本书依赖英语(和一定程度少量的其他欧洲语言),这是一开始就要交代清楚的。我也许可以通过指出当材料如此丰富,梳理不同语言的史学之困难来为自己辩解,不过我只想说由于缺乏语言技能,并易于获得熟悉的资料,造成了从初始就有偏见的结果。”
列洛教授遇到的问题是几乎所有从事世界史,尤其是全球史研究的人都有可能遇到的。文化上的隔膜、学术背景不一致、语言的多样性等使得世界史研究异常艰难,除了个人的努力之外,团队合作也是消除上述障碍的重要途径。80年代初吴于廑先生在武汉大学成立十五六世纪世界史研究室,研究室成员包括从事西欧、日本和中国史研究的专家学者,目的就是希望研究不同地区或国别、具有不同语言技能的学人通力合作,优势互补,以便写出真正具有整体性的世界史。今天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的条件比过去好多了,而且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越来越多西方国家的高校希望同我国建立学术交流与合作关系。
事实上,在诸如棉的全球史、丝绸之路世界史研究方面,我们中国学者拥有不少相关资料,完全可以和外国学者开展对话与合作研究。总之,由于历史上民族史与世界史的长期对立,英国和中国的世界史都发展缓慢。但进入21世纪以来,受全球化局势和史学自身变化的影响,两国的世界史都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但是,要消解民族史与世界史对立的影响,使我国的世界史成熟发展并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包括重视具体问题研究和实证研究,努力提高自身专业研究水平;将个人的具体研究放入世界历史大背景中,开展历史比较研究;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建设世界史学术共同体等。
